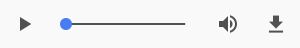
张玉川永远记得20世纪80年代那个高粱红透的傍晚。晚霞泼洒在天际,灿若桃夭。他一手执鞭、一手拉着牛撇绳,踩着木耙耙地,老牛慢吞吞地走着,耙齿翻起的泥土散发着清香与甘甜混杂的气息。高考落榜后的这些日子,他跟着父亲学会了犁田耙地,手掌磨出了新茧,心里却空落落的。
“玉川、玉川。” 声音从田埂那头传来。是邻村在高中教书的黄老师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的黑色人造革包在夕阳下泛着浮光。
“农业高中明年起实行对口招生,高考时不考英语,正好弥补你的弱项。”黄老师抹了把汗,接着说,“小梅下周就不代课了,今年也去复读”。
小梅是黄老师的小女儿,和玉川同窗十余载。今年村小学开学时,她在小学代课。此时,她抱着教案站在父亲身后,朝玉川浅浅一笑。那笑容虽轻,却确确实实唤醒了埋在玉川心里的那粒种子。
不知是喜讯来得突然,还是因为小梅的笑容,玉川突然觉得心里充盈着一股暖流,仿佛又握住了开启新人生的钥匙。
农业高中的日子比想象中充实。每天早饭后的空闲时间,黄老师总给玉川和小梅开小灶,安排他们在办公室背古诗。一次,小梅念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他们目光相遇的刹那,玉川觉得整间办公室都明亮起来。
学校每两周集中休息两天。第一个周末,大多同学思家心切,等不得第二天上午才有的班车,竟结伴步行回家了。走了十里路后,同行的陆续到家,只剩下玉川和小梅两人。月光将土路照得发白,路旁沉甸甸的高粱穗在风中沙沙作响,像在窃窃私语。
又一个周末,黄老师让玉川骑他的自行车回家。小梅说想妈妈了,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途中,她的手轻轻抓着他玉川的衣角说:“我爸说你明年一定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此时,只顾埋头蹬车的玉川,心跳得像擂鼓,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车轮碾过土路沙沙作响,像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可命运总在鲜花盛开的前夜降下霜冻。深秋时节,玉川的父亲猝然病逝。他一进家门,见76岁的爷爷蹲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地卷着旱烟,母亲哭得站不稳,14岁的妹妹搀着她。办理完父亲的丧事,正赶上秋收大忙。
一天,在附近收割豆子的小梅远远看到玉川赶着家里那头黄牛犁地,便走了过来。
牛是原来生产队的老牛了,分田到户时就跟了张家,五六年来耕种从不偷懒。
小梅见玉川赤着脚劳动,轻声问:“怎么不穿鞋,不怕豆茬扎了脚?”玉川用脚板在松软的土地上蹭了蹭说:“这样方便。”其实他是舍不得穿母亲新纳的布鞋。
母亲送来茶水时,留意到小梅关注儿子的眼神,眼睛突然亮了。她拉着小梅的手不放:“走,到婶子家吃饭,咱包饺子。”
待母亲和小梅离开后,玉川继续犁地。老牛却突然前腿一软,跪倒在地,一会儿工夫,肚子像吹气一样胀起来,没过多久就断了气。
20世纪80年代,耕牛不仅是耕作的依靠,更是一个农家主要的财产支柱。玉川的母亲闻讯赶来,抚着牛脖子慢慢蹲下,用袖子轻轻拭着止不住的眼泪。妹妹、弟弟毫无掩饰地哭出声来。爷爷看事已至此,红着眼圈拍拍玉川的肩膀:“去请屠户吧。”又朝母亲挥挥手说,“回家烧火做饭吧,日子该咋过还要咋过。”
爷爷还特意朝小梅笑了笑说:“家里那头小牛犊明年就长大了,就能接着力。”
就这样,作为家中长子的玉川,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默默继承了父亲那种最原始的犁地打场、摇耧撒种的生活。他把那些课本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底,像埋葬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梦。
转眼第二年七月,小梅考上了地区农校。临行那天,玉川在地里砍高粱。刨撅起落间,他忽然明白了——这满地的高粱,既是现实的藩篱,也是生活的希望。火红的高粱穗在阳光下摇曳,像在为他指引着另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作者单位:河南正阳农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