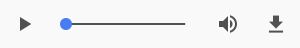
黎明悄然而至,黑幽幽的大树如同坚实的壁垒,这时候的天空也变成了灰白色,老刘望着窗外晃动的树影,身体就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外面的狗也隔着院墙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老刘索性起了身,披上一件衣服,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书房。
老刘的书房不大,放了一张老式办公桌和一把藤椅后,就只容得下转身的地方了。他走到桌前,想起了四十年多年前的自己。
四十多年前的老刘还不到二十岁,他挑着担子,一头放着老母亲为他缝制的棉被,另一头装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就赶去信用社报到。老刘的第一站在边远山区的一个信用社,那时候的信用社员工基本上靠脚底板丈量山乡,社里有位年近五十的老主任,那天他正在帮乡亲们搞秋收,两个裤腿卷到膝盖,上面沾满了泥土,顶着一张被太阳晒得黢黑的脸站在田坎上冲着老刘微笑着。
没到一个月,信用社老主任就带着年轻的老刘和周边的乡亲熟络起来。镇上的供销社送给老刘一张办公桌,桌子又大又重,他们借了拉货的板车,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桌子拉到信用社里,可是进柜台的门太小只能将桌子摆在营业厅,直到信用社第一次翻新时才将这张桌子搬进柜台,可是桌子没搬进去多久,老刘就被派到其他地方的信用社当会计去了。
信用社老主任退休的那一年,老刘又被调到这个镇上接了老主任的“班儿”。收拾办公室的时候,老主任说,这些桌子椅子都旧了,打个报告买些新的回来吧。老刘指着那张破旧得已经无法看清原来样子的桌子说:“那是咱俩费了好大工夫才搬回来的,赶明儿请个漆匠重新补补漆,再找个木匠把几个抽屉和把手修理一下,缝缝补补又三年。”于是,这张本来不用的办公桌又陪着老刘熬了几年,等到社里再一次装修,这张老式的办公桌怎么看都显得格格不入,一起工作的小年轻都劝老刘把它扔掉,老刘舍不得,喊上几个人又把它搬回离单位不远的老家。
老刘摸了摸早已凹凸不平的桌面,从衣服的前兜里掏出一副老花镜,慢慢地坐了下来。他弯下腰,打开书桌最底部的抽屉。也许是很久没有打开过,又或许是桌子过于老旧,拉的时候,抽屉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再用些力抽屉就会散掉,老刘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枚小小的私人印章来。
这枚印章是信用社老主任给老刘刻的,交给老刘的时候,老主任说这就是信合人的责任,就是信合人的命。有一次,老刘跟着老主任下村,不小心将印章落在老百姓家里,老主任把老刘的背包翻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呵斥着老刘挨家挨户地找,找到印章的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一老一小两个人淋着雨,深一脚浅一脚摸着黑往信用社赶,回到社里的老刘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夜。从那以后老刘特别小心,他在印章后面钻了一个洞用蓝色毛线穿起来每天都挂在自己的裤腰带子上。
老刘看着这枚印章,想着年轻时的囧事,微笑着摇了摇头,接着又从里面抽出几把老算盘。随着业务的发展,计算的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当年如同管家一般的大算盘是信用社的标配,逐渐被计算器取代,老刘在杂物室的角落里发现了这些木算盘,他不忍心又将他们捡了回来。
桌子的右上角放着一只棕色的箱子,里面放着这么多年老刘获得的奖状证书证和他曾经帮助的一个孩子给他的来信。那个孩子是老刘在下村走访时遇到的,除了一个年迈的爷爷身边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到该上学的年纪,却还在村里漫无目的的闲逛着,老刘看着心疼,主动为她联系学校、申请补贴,还经常寄给她一些生活费。孩子话少,就一封接着一封给老刘写信。此时,老刘扶着眼镜,又认真地读起了孩子的来信。当孩子难过的时候,他还是会皱起眉头;当孩子开心的时候,他还是会会心一笑;当孩子在信中提到申请加入共产党时,老刘急忙打开另一个抽屉,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枚党员徽章,轻轻地抚摸着,那颗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这时候的天已经亮了,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台偷偷溜了进来,在老刘脸上荡漾着,老刘笑着笑着就流下泪来。
就在今天,老刘退休了。
(作者单位:湖南桑植农商银行)







